胡正刚,1986年生,姚安县龙岗观善街人,云南省作协会员。在姚安一中读书期间,热爱文学创作,为《荷城文艺》骨干作者。之后外出求学、工作,仍笔耕不辍,在《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中国诗歌》《诗潮》《扬子江诗刊》《边疆文学》《滇池》等报刊发表过作品。2012年参加首届《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笔会;2013年获云南省 “百家”文学奖;2015年获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和楚雄州马缨花文艺创作奖。现居昆明。
今悉,胡正刚诗作《身体里的声音》入选2017年《新华文摘》第8期。该选刊有刊中“大哥大”之誉,入选之机会微乎其微。姚安有幸,正刚有幸!欣喜之余,为之祝贺,并公开,鼓我姚安士气。(饶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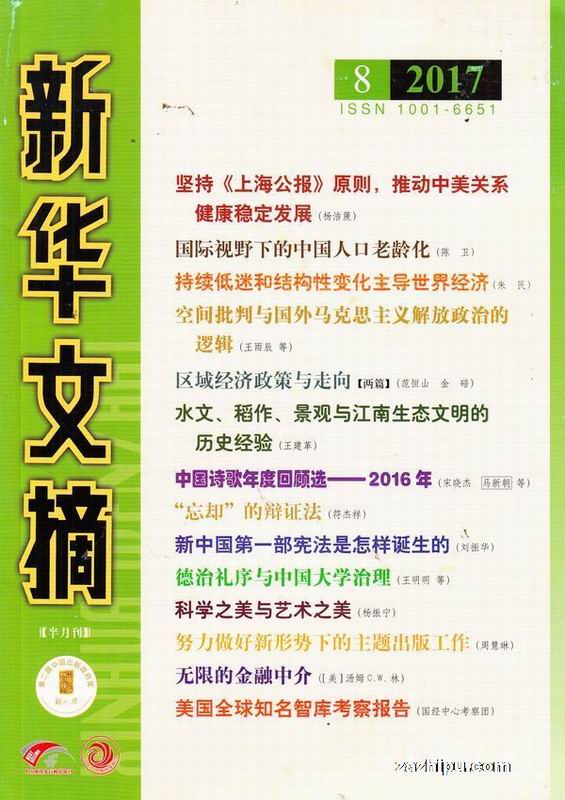
附:
身体里的声音
胡正刚
存在,但无法被叙述,这身体里的闷响
掷地有声,但行踪成谜。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它们只是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假想敌
因走投无路,已被光阴的刀刃驯服。
2009年秋天,暴雨过后,站在金水河边
看淘金人筛沙,沙子摩擦金属的声音
同时在我的骨缝里响起。2010年夏天
沿着红河赶路,流水声顺着芒果树漫上坡岸
穿过我的身体,在不知名的某处回荡
同年秋天,夜宿虚凝寺,暮色四合
敲钟人立于大殿外,一边念经一边敲响铁钟
梵唱和钟声,在我心底引起巨大的轰响
无法名状的痛击中,有什么轰然坠地
落在虚空荒芜之处……
多么令人绝望,一个无处藏身
却始终幻想着逃亡的人,连睡梦中
都充斥着一阵高过一阵的磨刀声
颜炼军短评:
一首倾听声音、倾听存在的诗。金沙磨擦的声音,流水的声音,古寺的钟声,以及与之对应的来自“我”身体里的“闷响”。当世界从符号、从陈词滥调“退回”感觉和存在,诗人的倾听就变成了命名。命名的立场,即是对诗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发明。这首诗里,这一立场虽然不够锐利,却已经表明诗人“磨刀”的努力。
一个推石头的人/赵丽兰
胡正刚说,有一次回姚安,朋友在县城为他洗尘,他提前把自己喝醉,才有勇气回乡,去面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面对故乡和内心,他纠结、矛盾、无能为力,却又被一种温暖的情怀所驱使,驱使着他一次次回到故乡,回到内心。他无处可逃。故乡给了他泥土,甚至为他准备了种子,只等他接纳这粒种子。
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在故乡的路上,一次次离开,又一次次返回。他在无数次往返的路途上乐此不彼。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因为偏执,所以幸福。在往返的路途中,他选择面对故乡的满目疮痍。即使选择的是醉了姿态,同样完成了心灵的救赎。没有逃避,便是勇气了。就像王单单在一首诗中写的:胡正刚憨厚老实,让他周而复始/将山上的礁石,推至山顶/再滚入水中。这种看似偏执的顽固,实则是一种坚守。他在往返的的姿态中让自己从失望的本质中逃离出来,找到了自己或者故乡的价值。不管他看上去如何笨拙,在醉或不醉之间,他动用的是真情。作为一个诗人,温暖和真情,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所以说,高高兴兴地推石头吧,故乡等着他回去。
这个推石头的小伙子,他动用的是真情和温暖。他的真情和温暖,却又暗藏着钝重的反击力。一不小心,就被一拳击中,一面喊疼,一面被打得浑身通泰。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笨拙,因为本身所具有的温暖和真情,可以让他以及他的诗,反复验证其朴实、憨厚、静观、重情、重义的本质。他的诗歌的底色,是暖色调的。这是基于他的真情而言,并非指简单意义的色彩的热烈、恣意和不管不顾。他笨拙地承认世界的荒诞,不借仁义理道来规范精神领域,忘掉儒家,成就了他诗歌的特质。笨得通透,诗歌就达到无为有处有无为的境界,大好。他诗歌里的暖,节制而有张力。温暖的底色上,有时他会放置一块石头,有时会生长一棵树,有时会燃一炷香。如果仔细寻找,更多的时候,会在他的诗歌里找到半剪月、一碗酒,或者一个着僧袍的老者。
这些暖调底色上的事物,让他和他的诗,有了不动声色的陡峭、担当和责任。在这个无序且喧嚣的尘世,谈担当和责任,显然,没有重量可言。然,胡正刚诗歌里的担当和责任,面对的是灵魂的多重性和人性的复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教科书里所理解的担当和责任。
龙华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故乡的版图上,灵魂的栖息之所。或者可以说,是他往返于故乡的精神所在,是出发,是归宿,是精神和诗歌的衣胞之地。龙华寺,在某种层面上,承载了纠结在他身体和精神里的矛和盾以及宿命所遭遇的空茫、无助、冷暖。在祈愿的路途上,只有借助黄连木、老和尚、念珠、经书来寻找身体的存在和心灵的救赎。裹一袭袈裟,固执而冷静地面对宿命满目的疮痍。借那一抹暖意,在空旷的时空中得于听见神的旨谕和回音。在《龙华寺手札之一》中,他写道:和尚的手,颤抖得有些厉害/“心无着落的人那么多/寄往天国的信件,有增无减/往来于天界和人间的邮差/会不会忙不过来?中途丢失。以其说他的诗歌借宗教之力为尘世心无着落的人们搭建了一把精神的阶梯,不如说其精神性的呈现是忠实于内心的凸显。每个人,都有两个灵魂,一个存在于现世的各种功能之中,比如穿衣、吃饭、上班、开会、房贷、工资等,更或者,存在于空而无当的悲悯、担当、批判、揭露、价值……一个温暖而透明的诗人,必是优秀的,优秀的诗人,其真实的另一个灵魂,呈现的,必是秩序里的价值和担当所无法懂得语言。一首诗能呈现什么,是假大空的谎言,还是卑如草芥裸露在霜芽上的白。在人类文明的延展中,寺庙是精神的皈依之地,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龙华寺,在胡正刚的诗歌里,承载的便是这个意义上精神的原乡。
在胡正刚的诗中,故乡,是特指,更是泛指。他所走过的土地、山川、河流、寺庙,所遇到山林草木、鸟兽虫蚁都是他的亲人,都是他的故乡。他从龙华寺或者姚安这个精神的原乡出发,背一罐酒、执一根木杖,往返于故乡的路途中,不断地寻找、追溯,有时是漫无目的孤魂一般的游荡。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早早地就宿命一般地以西西弗斯式的固执,或静观或内省地面对工业时代的机器在“故乡”的身体上挖掘而出的洞坑。
红河、蛮耗、哀牢山、陇川……这些他走过的地方,无一不是他的故乡。这些在故乡大地上遇到的亲人,以及说是影白、普文忠、俐侎老人,不如说是他自己,更恰如其分。甚至在陇川遇到一根甘蔗,以及一根甘蔗的甜,也是他自己。每一株甘蔗,都是一道通往白云的楼梯/又怕一脚踩空,再也回不到故乡//在陇川,雨水让我萌生了太多妄念/也让我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心里长满黄连和苦蒿的人/那么多山水,那么多动荡不安的旅程/每走一步,心上的螺丝,就拧紧一圈/真的不能再继续往行囊里,塞进苦和涩了/刚产生剥开一株甘蔗的想法,它的甜/已经让我心慌手抖。什么样的“甜”,会让诗人心慌手抖。在此,诗人让一棵甘蔗开口说话,开口说出的不是甘蔗本身的甜,而是“甜”以外一个时代的动荡不安与喧嚣麻木。诗人通过一根甘蔗,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某个剖面的横切,甚至将这个横切的剖面,还原为一个时代无可言说的荒谬。“甜”和“甜”所产生的荒谬或虚无,无疑不是戏剧性的,它令我们所难过的是,一根甘蔗所呈现的是与“甜”无关的味道。陇川的这根甘蔗,无疑是美妙的,妙则妙矣,奇苦无比。
在往返于故乡路途中,他还和一间单人牢房相遇。在《去茶山》中,他写道:怀揣诗稿赶路,漂泊无定的人间/你用手中的笔画过饼,画过/梅林,路过清汪汪的关河时/还在江水里,画过一间单人牢房。在清汪汪的河水里,他用黑笔,一笔一笔把牢房画成黑色。每个的心中,都有一间牢房,关着自己。这近乎绝对的方式,一定来自于生命极大的悲悯。
胡正刚用诗歌的方式,完成了往返于故乡路途中遇见的细微生命的过程。然而,这还不够。他是不安分的,他试图寻找到理想与现实之差,产生的那个时空之夹缝。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快餐的、速食的、短平快的。那些想慢下来的生命个体必须在快和慢之间找到一个时空,得于照见生命内里的本真。胡正刚的诗,在某个层面上无疑拓展了这个时空。他诗歌里的笨拙、真诚、憨厚,记录片一般真实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碎片化的影像。这还不够,他想让他和他所处的时空慢下来。他必须在往返于故乡的路途中,不停咀嚼反刍,并试图找到那个快与慢之间的时空,借于泅渡自我或和他一样彷徨的生命个体。这或许就是胡正刚诗歌的出发和归宿。快与慢之间的这个时空,如遗落于旷野上的一面镜子,拂去蒙霜的镜面,呈现遍体的荒诞、分裂和紧张。即便如此,他还是乐于要照一照,以此内观,以此照见夹缝中生命本真的状态。他贪恋并爱这个世界,并坦率地说出并承认这个世界的荒谬性。你在月光下给我写山水诗时/我会倒一碗酒,用碗里的月亮/做镜子,数额上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送普文忠回哀牢山》)。但你仍然一再低头,试图/用泪水稀释酒液。碗底的月光/却像一面镜子,烛照出尘世的悲辛(《除夕》)。拂去镜面上的霜迹,他反复观照。他在快慢之间照出的这个时空差,有意无意地接纳并重建了夹缝之中精神的空间感。然,这个空间无疑是局促的、患得患失的。这个时空差,一会真实,一会虚无。作为诗歌本身,作为给心找到的一个去处,其存在性却又是必须的,不置可否的。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里写到两面镜子,一面是快镜,一面是慢镜。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前将其照出,慢镜则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照出,慢镜落后的时间与快镜提前的时间相等。阿捷赫公主在镜中见到了自己闭着的眼睛,便立刻死了。快慢两镜一前一后照出了她眨动的眼皮。这样的构思非常巧妙。当然,胡正刚在他的诗歌中,并没有刻意这样构思。他天性的笨拙,决定了他不会花语巧语,也无需投机取巧。但是,他反复观照的姿态,和《哈扎尔辞典》里的快慢镜,却有异曲同工之效。他用两面镜子,快镜照见的是现世的碎片化与分裂性,慢镜照见的是精神领域里的自省、反诘、探究,甚至是刮骨疗伤,得于完成现世和精神的两相观照。
今年九月,我和胡正刚、雷杰龙、王单单、杨子人一起骑单车环了一圈抚仙湖。在海镜村,我们爬上一只铁皮船,朗诵诗歌。天阴着,黑夜的天幕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湖面上,零星闪烁着几点光亮,试图把光的生命全部呈现给一面湖水,是温暖的另一种命题。微弱的光亮里,我惊喜地看到了水中有小石头鱼。而胡正刚看到了却是:不敢学银鱼、白鹭和/秋风里摇曳的烟柳/不敢把湖水/当作照骨镜,害怕一眼/就看清骨子里藏匿的不安/动荡,以及一个悲观者的/穷途和末路(《在海镜村》)。显然,诗人看到的现世,不是目之所及的事物,而是心灵深处无奈的启示或拷问。他时时关照着一快一慢之间所产生的时空之差,并用诗歌的方式,为存在于夹缝中的这个时空发声,用寓言一般的祷词陈述尘世悖论。他的肯定,来自己于他的否定。他的否定,又发端于他的肯定。每次陈述和照见,都是内在秩序的摧毁或构建。
某一瞬间,我看见胡正刚把抚仙湖当作了他的故乡。这清晰地印证了他在往返于故乡的路途中西西弗斯式的固执。他诗歌中呈现的这种身份性并不模糊,相反,会愈加清晰。我并不担心他这种身份性的清晰度,也不担心他周而复始推石头的姿态。我担心的,是他推石头的时候,用力过猛。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我怕他受伤。我更愿意看到他弯腰拾起抚仙湖畔的一颗小石子,顽劣地向湖心扔去,在湖面划出一梭水漂的样子。

主 办:姚安县人民政府 承 办: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Copyright 2014 365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云南力诺科技有限公司
